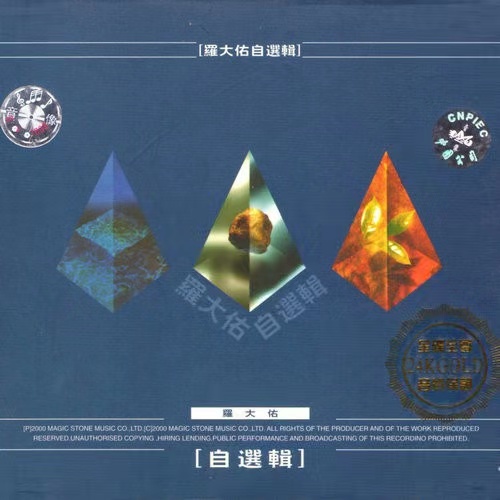这几天可真冷,听房东说应该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刻。记得以前住在东南部的时候没有这种体验。可能是那会儿我比现在年轻。
偶尔坐着他的车出去一下,高速公路两边远处的建筑和更远处的天空混合成一片深灰或浅灰。我麻木地看着这些草木山河,觉得那与己无关,它们没历史没文化甚至没有生命只是一动不动地存在着。可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只是我自己不去了解的懒惰与傲慢。在时间的维度中,任何地域的江山大河内外表里都是一样的。懒惰自不必说,我的傲慢来自于哪里?大概来自于从小读过的书,看过的画报,听过的话语。而现在,当我妹妹问我想不想回家的时候我只能说“乡愁”这个单词是Homesick,除过我挂念的那些人,留在心里的只有残存的Sick。
不小心发现已经进入腊月。于是想起来每年此时都会有人打招呼说已经替我腌好腊八蒜并在几天之内送到家来。对于别人这种无需提醒的挂念,我一直内心惶恐。我想给别人作一个好朋友,在自己力所能逮的地方为他人帮个忙,如果不行,至少不去添乱。如果添乱必不可少,那就来点小的,或者提前告诉对方好有个小小的准备。可我此刻的怀念只停留了四十五秒,就被自己剥出的大蒜熏跑了。
做梦的频率大增。可能是在我睡着之后,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我在酣睡,为了确认我在睡觉,用做梦来证明。另一个是我的意识,意识的我制造了梦。我入梦后,意识离开我的身体,我不知道作为意识的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在白天,大脑活跃时,意识的我服务身体的我。而在深夜,我的意识等身体休眠后,悄悄离开了,它以各种方式出现,时而是另一个人,有时是她迈着漂亮的步伐穿透我透明的身体,或者风和雨拍打我的窗子,企图将我唤醒。
预报有雪,雪前余风,碎旧伤逝,逃犯般窜过街头,这地方人口稀少,无论如何也鼎沸不起来,就连外卖店厨房里挤出的蒸汽都无精打采,缺氧似的。实际上,英格兰中部已颓废很久了。谁知道大雪并未如约而至,我的同事们假装告别了颓废,兴奋如日光返照,其实那日照没办法投射在我们99%的室内工作中,我们都不配尾随一个稀薄的影子。
总是在下班路上幻想,天天路过的某个巨大的街角那里应该有一个菜市场。我和她天天去买菜,跟老板混得飞熟。杀了鱼,顺便问下看上去擅烹饪的大姐,这鱼怎么弄才好吃,然后高高兴兴回家做给她,看她笑眯眯伸出筷子理直气壮去夹那块最细嫩的鱼肉。看她满心的爱意从那双好看的眼睛里面咕嘟咕嘟往外溢出。突然想起一个小小遗憾,应该在她生日时候再加一句给她,“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我觉得李志肯定是王家卫的粉丝。他那句“来到这个城市已经896天”是标准的王氏语气。我从去年三月七日从香港到英国到底过了多少天,算呀算却总是算不清。这个成了我一块心病,总觉得在老年痴呆袭击大脑之前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
天气越冷,就会越惦记带我爹去吃涮羊肉。大半盘红白相间的大片羊肉一口气入锅,略一变色夹出来沾上芝麻酱立刻入口。我这执念来自我爹年轻时候带我四处觅食的经历。我不管价钱贵不贵,分量多不多,只惦记好吃不好吃,也从来没想过我爹的钱包里面厚度够不够。可后来带我爹四处吃饭,他总会假装不经意问我一句,这顿饭花了多少钱?我对付他只有一招:忘了看支付宝账单,人家直接扫走了,又不会错,管它呢?!他不再追问,我也假装他不曾问过。
小时候我爹带我泡澡,必须答应路上顺带买点点心或炸鱼,我才肯去。长大我带我爹泡澡,把车专门停在小院门口,让我爹出门时候和老邻居打招呼时候告诉他们,我儿子带我去泡澡,然后听到大家夸赞羡慕的言语,他一脸得意的样子。他像领导一样坐在后排,手一挥,车就启动了,我知道他不是不愿意坐在前排和我聊天,而是嫌安全带勒着不爽。
英格兰的冬天雨水真多啊。粗略看去,似乎都是雷同的,红褐色的房子有着半黑的屋顶,在偶尔出现蓝天下,偶尔会有一只黑鸟或白鸥飞过。